浅谈神经网络中激活函数的设计
By 苏剑林 | 2017-10-26 | 50915位读者 | 引用激活函数是神经网络中非线性的来源,因为如果去掉这些函数,那么整个网络就只剩下线性运算,线性运算的复合还是线性运算的,最终的效果只相当于单层的线性模型。
那么,常见的激活函数有哪些呢?或者说,激活函数的选择有哪些指导原则呢?是不是任意的非线性函数都可以做激活函数呢?
这里探究的激活函数是中间层的激活函数,而不是输出的激活函数。最后的输出一般会有特定的激活函数,不能随意改变,比如二分类一般用sigmoid函数激活,多分类一般用softmax激活,等等;相比之下,中间层的激活函数选择余地更大一些。
浮点误差都行!
理论上来说,只要是非线性函数,都有做激活函数的可能性,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最近OpenAI成功地利用了浮点误差来做激活函数,其中的细节,请阅读OpenAI的博客:
https://blog.openai.com/nonlinear-computation-in-linear-networks/
或者阅读机器之心的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PBRzS4Ol_Zst35XKrEpxdw
更别致的词向量模型(三):描述相关的模型
By 苏剑林 | 2017-11-19 | 129170位读者 | 引用几何词向量
上述“月老”之云虽说只是幻想,但所面临的问题却是真实的。按照传统NLP的手段,我们可以统计任意两个词的共现频率以及每个词自身的频率,然后去算它们的相关度,从而得到一个“相关度矩阵”。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个共现矩阵太庞大了,必须压缩降维,同时还要做数据平滑,给未出现的词对的相关度赋予一个合理的估值。
在已有的机器学习方案中,我们已经有一些对庞大的矩阵降维的经验了,比如SVD和pLSA,SVD是对任意矩阵的降维,而pLSA是对转移概率矩阵$P(j|i)$的降维,两者的思想是类似的,都是将一个大矩阵$\boldsymbol{A}$分解为两个小矩阵的乘积$\boldsymbol{A}\approx\boldsymbol{B}\boldsymbol{C}$,其中$\boldsymbol{B}$的行数等于$\boldsymbol{A}$的行数,$\boldsymbol{C}$的列数等于$\boldsymbol{A}$的列数,而它们本身的大小则远小于$\boldsymbol{A}$的大小。如果对$\boldsymbol{B},\boldsymbol{C}$不做约束,那么就是SVD;如果对$\boldsymbol{B},\boldsymbol{C}$做正定归一化约束,那就是pLSA。
但是如果是相关度矩阵,那么情况不大一样,它是正定的但不是归一的,我们需要为它设计一个新的压缩方案。借鉴矩阵分解的经验,我们可以设想把所有的词都放在$n$维空间中,也就是用$n$维空间中的一个向量来表示,并假设它们的相关度就是内积的某个函数(为什么是内积?因为矩阵乘法本身就是不断地做内积):
\[\frac{P(w_i,w_j)}{P(w_i)P(w_j)}=f\big(\langle \boldsymbol{v}_i, \boldsymbol{v}_j\rangle\big)\tag{8}\]
其中加粗的$\boldsymbol{v}_i, \boldsymbol{v}_j$表示词$w_i,w_j$对应的词向量。从几何的角度看,我们就是把词语放置到了$n$维空间中,用空间中的点来表示一个词。
因为几何给我们的感觉是直观的,而语义给我们的感觉是复杂的,因此,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几何关系来反映语义关系。下面我们就根据我们所希望的几何特性,来确定待定的函数$f$。事实上,glove词向量的那篇论文中做过类似的事情,很有启发性,但glove的推导实在是不怎么好看。请留意,这里的观点是新颖的——从我们希望的性质,来确定我们的模型,而不是反过来有了模型再推导性质。
机场-飞机+火车=火车站
果壳中的条件随机场(CRF In A Nutshell)
By 苏剑林 | 2017-11-25 | 123897位读者 | 引用本文希望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把CRF(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的原理讲清楚,这里In A Nutshell在英文中其实有“导论”、“科普”等意思(霍金写过一本《果壳中的宇宙》,这里东施效颦一下)。
网上介绍CRF的文章,不管中文英文的,基本上都是先说一些概率图的概念,然后引入特征的指数公式,然后就说这是CRF。所谓“概率图”,只是一个形象理解的说法,然而如果原理上说不到点上,你说太多形象的比喻,反而让人糊里糊涂,以为你只是在装逼。(说到这里我又想怼一下了,求解神经网络,明明就是求一下梯度,然后迭代一下,这多好理解,偏偏还弄个装逼的名字叫“反向传播”,如果不说清楚它的本质是求导和迭代求解,一下子就说反向传播,有多少读者会懂?)
好了,废话说完了,来进入正题。
逐标签Softmax
CRF常见于序列标注相关的任务中。假如我们的模型输入为$Q$,输出目标是一个序列$a_1,a_2,\dots,a_n$,那么按照我们通常的建模逻辑,我们当然是希望目标序列的概率最大
$$P(a_1,a_2,\dots,a_n|Q)$$
不管用传统方法还是用深度学习方法,直接对完整的序列建模是比较艰难的,因此我们通常会使用一些假设来简化它,比如直接使用朴素假设,就得到
$$P(a_1,a_2,\dots,a_n|Q)=P(a_1|Q)P(a_2|Q)\dots P(a_n|Q)$$
分享一个slide:花式自然语言处理
By 苏剑林 | 2018-01-23 | 88006位读者 | 引用基于CNN和VAE的作诗机器人:随机成诗
By 苏剑林 | 2018-03-24 | 136879位读者 | 引用前几日写了一篇VAE的通俗解读,也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认可。然而,你是否厌倦了每次介绍都只有一个MNIST级别的demo?不要急,这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更经典的VAE玩具:机器人作诗。
为什么说“更经典”呢?前一篇文章我们说过用VAE生成的图像相比GAN生成的图像会偏模糊,也就是在图像这一“仗”上,VAE是劣势。然而,在文本生成这一块上,VAE却漂亮地胜出了。这是因为GAN希望把判别器(度量)也直接训练出来,然而对于文本来说,这个度量很可能是离散的、不可导的,因此纯GAN就很难训练了。而VAE中没有这个步骤,它是通过重构输入来完成的,这个重构过程对于图像还是文本都可以进行。所以,文本生成这件事情,对于VAE来说它就跟图像生成一样,都是一个基本的、直接的应用;对于(目前的)GAN来说,却是艰难的象征,是它挥之不去的“心病”。
嗯,古有曹植七步作诗,今有VAE随机成诗,让我们开始吧~
模型
对于很多人来说,诗是一个很美妙的玩意,美妙之处在于大多数人都不真正懂得诗,但大家对诗的模样又有一知半解的认识。因此,只要生成的“诗”稍微像模像样一点,我们通常都会认为机器人可以作诗了。因此,所谓作诗机器人,是一个纯粹的玩具了,能作几句诗,也不意味着普通语言的生成能力有多好,也不意味着我们对NLP的理解有多深。
CNN + VAE
就本文的玩具而言,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主要是把一维CNN和VAE结合了起来。因为生成的诗长度是固定的,所以不管是encoder还是decoder,我都只是用了纯CNN来做。模型的结构图大概是:
从最大似然到EM算法:一致的理解方式
By 苏剑林 | 2018-03-15 | 164280位读者 | 引用最近在思考NLP的无监督学习和概率图相关的一些内容,于是重新把一些参数估计方法理了一遍。在深度学习中,参数估计是最基本的步骤之一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模型训练过程。为了训练模型就得有个损失函数,而如果没有系统学习过概率论的读者,能想到的最自然的损失函数估计是平均平方误差,它也就是对应于我们所说的欧式距离。而理论上来讲,概率模型的最佳搭配应该是“交叉熵”函数,它来源于概率论中的最大似然函数。
最大似然
合理的存在
何为最大似然?哲学上有句话叫做“存在就是合理的”,最大似然的意思是“存在就是最合理的”。具体来说,如果事件$X$的概率分布为$p(X)$,如果一次观测中具体观测到的值分别为$X_1,X_2,\dots,X_n$,并假设它们是相互独立,那么
$$\mathcal{P} = \prod_{i=1}^n p(X_i)\tag{1}$$
是最大的。如果$p(X)$是一个带有参数$\theta$的概率分布式$p_{\theta}(X)$,那么我们应当想办法选择$\theta$,使得$\mathcal{L}$最大化,即
$$\theta = \mathop{\text{argmax}}_{\theta} \mathcal{P}(\theta) = \mathop{\text{argmax}}_{\theta}\prod_{i=1}^n p_{\theta}(X_i)\tag{2}$$
变分自编码器(二):从贝叶斯观点出发
By 苏剑林 | 2018-03-28 | 520767位读者 | 引用源起
前几天写了博文《变分自编码器(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从一种比较通俗的观点来理解变分自编码器(VAE),在那篇文章的视角中,VAE跟普通的自编码器差别不大,无非是多加了噪声并对噪声做了约束。然而,当初我想要弄懂VAE的初衷,是想看看究竟贝叶斯学派的概率图模型究竟是如何与深度学习结合来发挥作用的,如果仅仅是得到一个通俗的理解,那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我对VAE继续思考了几天,试图用更一般的、概率化的语言来把VAE说清楚。事实上,这种思考也能回答通俗理解中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重构损失用MSE好还是交叉熵好、重构损失和KL损失应该怎么平衡,等等。
建议在阅读《变分自编码器(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后对本文进行阅读,本文在内容上尽量不与前文重复。
准备
在进入对VAE的描述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性的内容讲一下。
从动力学角度看优化算法(二):自适应学习率算法
By 苏剑林 | 2018-12-20 | 53326位读者 | 引用在《从动力学角度看优化算法(一):从SGD到动量加速》一文中,我们提出SGD优化算法跟常微分方程(ODE)的数值解法其实是对应的,由此还可以很自然地分析SGD算法的收敛性质、动量加速的原理等等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去理解优化算法中的自适应学习率算法。
RMSprop
首先,我们看一个非常经典的自适应学习率优化算法:RMSprop。RMSprop虽然不是最早提出的自适应学习率的优化算法,但是它却是相当实用的一种,它是诸如Adam这样的更综合的算法的基石,通过它我们可以观察自适应学习率的优化算法是怎么做的。
算法概览
一般的梯度下降是这样的:
$$\begin{equation}\boldsymbol{\theta}_{n+1}=\boldsymbol{\theta}_{n} - \gamma \nabla_{\boldsymbol{\theta}} L(\boldsymbol{\theta}_{n})\end{equation}$$
很明显,这里的$\gamma$是一个超参数,便是学习率,它可能需要在不同阶段做不同的调整。
而RMSprop则是
$$\begin{equation}\begin{aligned}\boldsymbol{g}_{n+1} =& \nabla_{\boldsymbol{\theta}} L(\boldsymbol{\theta}_{n})\\
\boldsymbol{G}_{n+1}=&\lambda \boldsymbol{G}_{n} + (1 - \lambda) \boldsymbol{g}_{n+1}\otimes \boldsymbol{g}_{n+1}\\
\boldsymbol{\theta}_{n+1}=&\boldsymbol{\theta}_{n} - \frac{\tilde{\gamma}}{\sqrt{\boldsymbol{G}_{n+1} + \epsilon}}\otimes \boldsymbol{g}_{n+1}
\end{aligned}\end{equ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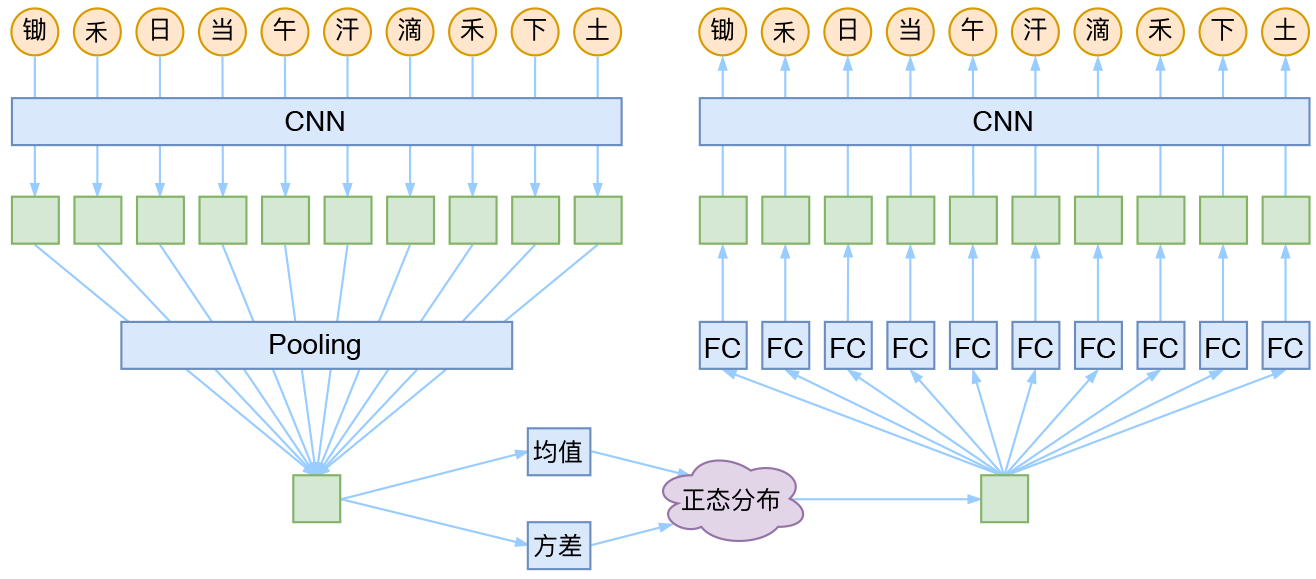

最近评论